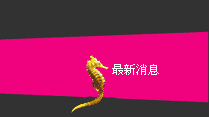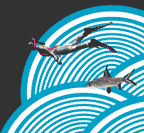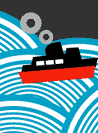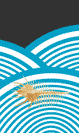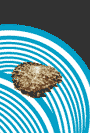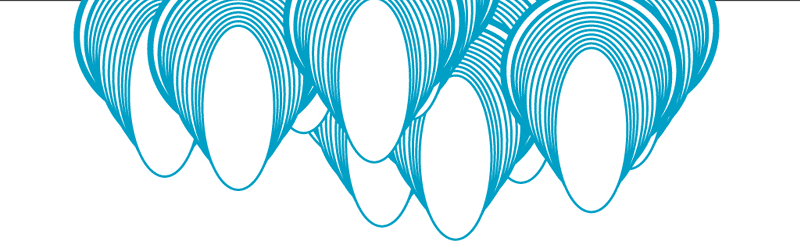「2003第三屆南方影展」
-百花齊放、萬紫千紅
李幼新
人生在世不快樂。
2003年夏秋,我先後擔任「金穗獎」的評審與「南方影展」競賽片初審評審見識到那麼多的才華、創意與關愛,各家各派的努力耕耘(在社會、在生命、在心靈、在藝術…)開拓我的視野、啟發我的思路、讓我經驗一次又一次的、一種又一種的學習旅程。只是,任何電影獎與電影展都有量的限制,不可能把所有參賽影像照單全收(果真來者不拒或許不切實際,會讓觀眾看得不勝疲累、招架不住而錯失一些作品),濫情如我,總覺得各有各的好,人人可以是我師,褒貶取捨具讓我痛苦不堪。
舉例來說,台灣的這個哪個電影競賽在紀錄片項目都有不少是用導演自己家人當作題材的觀察、描述與探討,許麗善的《阿母》比起許多參賽對手,在形式上或許並不格外奇詭。但是當女兒伴著媽媽坐在地上,說到正在錄影,媽媽笑得欣慰更笑得天真,那「真情流露」的神架讓我感動也讓我銘記。又譬如,我對登山不是那麼感興趣,半時電影看了也不會輕顯被蘇彥彰的《下不來的直昇機》把山野雲天拍攝得美美的而有啥驚喜(不過倒讓我會為自己的不愛登山而遺憾平白錯失大自然的美景,算是觀影的而外收穫),但是錄影帶(從開場算起)大約跑到65分鐘時,三位男孩游泳的畫面被zoom-out既展現大自然湖光山色美得出奇又不著片言隻字顯示人的渺小,我還是被逮住了、被陷下去了。雖然「Chu+O」(朱家麟)的劇情短片《夢》有點像音樂錄影帶又好似實驗短片,雖然slow
motion也不是他發明得,我卻為了海浪在歌聲中的慢動作般四散,而像紗、似煙、如詩如「夢」(而切題),而撩起我對「非理性的」、「不連續的」…種種「夢」的特質的聯想。也就是說,落選就並不一定是整體不好,更非連局部都一無可取。不單是入圍片,也不僅是將來決選得獎片才給我啟發、讓我賺到,而是所有參賽作品共同豐富了我的生命、愉悅了我的眼睛。
近期胡台麗策劃、映演的「2003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引進了法國紀錄片大師與人類學家尚.胡許(Jean Rouch)四十多年前的名作。台灣有影評人用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與類似後殖民的論述質疑身為白人的胡許拍攝非洲黑人族群時可能的(不自覺的)白人沙文主義與搶著代言的危險。我喜歡這樣省思(其實那位影評人更應該去檢討法國導演楚浮當年不屑看印度導演薩提雅吉.雷的電影!),不過我也不敢忽視現在芸芸眾生的白人導演都無意或不屑去、去了解、去呈現非洲黑人生活與想法時,胡許卻像先驅般的勇氣與辛勞。我不全然茍同那位影評人,是一方面揣測白人佔盡種種資源優勢使得黑人用影像呈現自我族群可能因而遲緩多年,另一方面卻憂慮某些現象不可一概而論。請問那位影評人是不是也會指責李道明、胡台麗、鄭文堂在台灣原住民題材的電影上以漢人的優勢搶了原住民自己用影像背聲的先機呢?這種批鬥與苛求完全忽視了李道明、胡台麗、鄭文堂放棄漢人與知識份子的身段。以及毅然開拓冷僻題材多年耕耘的苦心。從這屆「南方影展」(以及「金穗獎」)參賽的各方俊傑秀逸來看,原住民的影像人才不但激增,原住民議題的影像創作也百家爭鳴。我覺得恰似女性議題與同志議題的電影,永遠不會嫌多,重要不在多不多的問題,而是拍得好不好的問題。有時,我不免遐思,真希望有人能發表論文分析論述當今原住民導演們的完住民題材影像創作,跟李道明、胡台麗、鄭文堂拍攝原住民影像的異與同。其實,我這種想法本身就很沙文主義。為什麼要把漢人導演們像明星般各個區隔,把原住民導演們卻當成一個整體來對應呢?難道每位原住民導演們彼此間就不能有形式上、風格上、內涵上…的明顯差異嗎?這種態度,豈不跟美國白人觀眾(以及台灣觀眾)都能分辨奧黛麗赫本、伊麗莎白泰勒、碧姬芭杜、茱麗亞羅勃玆…的各自特色,卻把非洲黑人演員當成天下烏鴉一般黑,不但記不清每張臉的差別、甚至不知道人家的名字。
陳俊志長期拍攝同志題材、蔡崇隆關切冤獄與司法不公、及白色恐怖的歷史、董振良好像永遠是金門人在講金門事…,我固然尊敬這樣的熱情與奉獻,但是我們也應該允許導演們去開發、去嘗試、去研發其他的族群、別樣的議題。馬耀.比吼就交出了光耀的成績單,既在原住民歷史的《揹起玉山最高峰》大放異彩,又在台灣的浙江大陳移民遊走台灣、美國、中國間生動鋪陳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來去大陳》。這次「南方影展」邀請觀摩的台灣作品中,李道明聚焦泰國勞工的《離鄉背井去打工》是紀錄片的榮作也是台灣難得一見的工人運動電影,原住民導演們的百花齊放反倒使得鄭文堂更樂於並肩作戰繼續他最鍾愛的原住民族群與影像,而讓《風中的小米田》溢滿他的深情與詩情。
蔡崇隆以《島國殺人事件Ι-蘇建和案》享譽,他對警方(涉嫌)刑求逼供的合理懷疑、對司法不公的控訴、對人權維護的無視時間與空間帶給他的折磨與歷練,總是讓我也讓台灣人權協會由衷感佩。我總覺得,台灣解嚴多年,當今甚至堪稱亞洲最民主的地方,只是,從某些學校對學生的髮禁到軍中人權(與依然保留徵兵制)到刑事警察們的不擇手段的刑求逼供、冤獄頻頻(請問台灣的刑警、檢察官、法官要怎麼解釋一案兩破的荒謬現象?能不承認冤獄的確存在與民主/司法的恥辱嗎?)卻依然停留在白色恐怖的武裝時代。雖然人人都可以怪罪蔣介石的威權獨裁鼓勵了也造就了這些現象(寧可錯殺千萬也不錯放一人!),但是解嚴多年政治與司法也該有點長進,與其繼續歸咎歷史,何不徹底改革?蔡崇隆的《島國殺人事件Ⅱ-盧正案》無論已被搶決的盧正是否有罪,起碼警方、檢察官、法官的各方瑕疵疑點重重惹人詬病,較誰能相信不是冤獄而死的呢?導演在社會關懷、認真探索得見深度與智慧外,還有讓人眼睛一亮的影像省思。譬如家屬去法務部陳情,警察出面干涉,但因媒體與攝影機相隨,你我見識到警察(以及官員)笑面虎般低姿態的偽善。又如本片讓你體認刑警問案或是完全不錄影存證、或是沒有全程錄影(只是選擇性錄影!)、或是縱然全程錄影卻提供經過刪減與粉飾的片段以偏概全!男導演蔡崇隆還拍攝過台灣腦性麻痺青年黃乃輝與柬埔寨少女強娜威的婚姻/愛情糾葛紛爭的紀錄片《我的強娜威》(剛在「民族誌影展」放映過),女導演溫知儀也拍攝了同一題材的紀錄片《兒戲》(剛在「2003女性影展」台北地區放映過)。兩個版本各有各價值與意義,或許像沈紘騰(他是蔡崇隆許多作品的攝影師與剪輯師)與顧玉珍說的兩片差別一是宏觀、一是微觀,黃乃輝的身體是台灣弱勢、強娜威(女性以及貧苦國度)是國際弱勢。觀察有人認為女導演似乎比較同情黃乃輝而男導演反而更願意傾聽強娜威發聲。我認為這樣更好,兩位導演都超越了自身的性別,等於是女性主義的兩種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