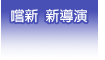|
「嚐新・新導演」何蔚庭 Ho Wi Ding 介紹
|
風中的漂流影者
|
風相星座的何導演出生於馬來西亞,在高中時即與電影結緣。當時他們鎮上有三家戲院,播放的全是好萊塢電影和港片。往往一些票房較差的影片很快就被下檔,但何導演的父親告訴他:「演一天的戲反而是最好看的」,因為這些票房差的片子往往都是藝術價值比較高的影片。而由於影片遞換速度快,能看到的片子就自然增加了;何導演悠遊其中,在這些戲院裡灑落不少青春時光。當時的何導除了對電影感興趣,也會自己寫影評、投稿賺戲票。
|
 |
|
十八歲的他漂洋過海到加拿大留學,為年輕的生命展開不同的視野。曾在多倫多的York
University唸了一年的Fine
Arts,但覺得那不是他所想要的。也許是風相星座的個性使然吧!何導演認為只要覺得不喜歡或不適合,就會想要改變。離開加拿大後,便到洛杉磯繼續升照,暑假便在美國的南加大(USC)修習電影相關課程,但南加大的環境不適合他,因為他們比較重工業性,傾向把你推向好萊塢;後來接觸紐約大學(NYU),發現他們就比較多元一點,也比較鼓勵創作,像賈木許(Jim
Jarmush)、李安(Ang Lee)、史派克李(Spike
Lee)風格都很不同。於是之後只申請了紐約大學電影系即順利被錄取,自此才真正開始電影製作的學習和創作生涯。
從馬來西亞到加拿大、紐約,繞了半個地球之後到了新加坡為發現科學頻道(Discovery
Channel)拍廣告,何導演卻又決定轉移到台灣
。當初會來到台灣主要是新加坡的環境不適合。雖然沒來過台灣,卻斷然選擇來這裡是因為有一個在政治大學唸書的妹妹。事後覺得選擇台灣是對的,因為台灣比較具有生命力,就像紐約一樣,因此何導演很快就能適應。
至今何導演已在這個島嶼上創作有四年之久,繼續拍攝廣告、紀錄片、短片及MTV。對於是否會再轉移到其他國家拍片,他表示:「現在年紀比較大了,比較穩定了。」
出走•回歸
同樣為馬來西亞籍的華人導演蔡明亮,明年將在大馬開拍新片《黑眼圈》;而何導演是否也想回大馬拍片呢?對於這個問題,何導演給我們上了一堂“大馬電影入門”課。他表示:馬來西亞主要由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三個族群組成,但政權主要還是落在馬來人手中,很多的政策與國際形象的營造皆以馬來人為主。馬來西亞的電影以馬來西亞語片作為官方影片,而如果影片拍的是華人,他們會說不符合國情,不但不會給予補助,電檢時也可能會刁難你,例如今年亞太影展,某部大馬影片在備受壓力之下退出參展,是相同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何導演表示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所以一些比較親密的鏡頭都會被剪掉或直接跳過。由此可見為何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參展亞太影展,卻無法放映的奇怪現象。何導演認為不排除將來回大馬拍片的可能性,但也許要像蔡明亮,拍了多部電影得到國際認同之後才回大馬拍片。
相形之下,台灣就給予創作者較多的空間。當初《呼吸》報名參展時,新聞局剛開始擔心何導演國籍問題會造成爭議,但後來何導演找到台灣公司代表出品,就解決了問題,比起馬來西亞彈性算大很多了。台灣政府在政策上、制度上的支持,除了有助本土電影的復甦,也讓台灣成為華人電影發展的重要一站。
類型•風格的迷思
對拍電影,何導演有他的一套想法。他認為其實藝術片賺錢就是商業片,像《艾蜜利的異想世界》。商業片也有一定具有藝術價值,
像《魔戒》或杜琪峰的《黑社會》 。他認為當導演選擇拍片題材可以有彈性一點,就像墨西哥導演Alfonso
Cuarón的作法,之前拍《你他媽的也是》(Y tu mamá también)後來導的是商業影片《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至於本身對影像風格塑造的看法,何導演認為一個導演的風格都是別人判定的。風格的存在,其實對導演而言並不清楚,它通常是根據直覺發展出來的,而不是刻意塑造,就像賈木許拍的片就是賈木許的影片。同時,何導演也表示:「風格有時是因為環境而造成的,有些東西你製作的環境不對,怎麼玩風格也無法。」何導演說:「像王家衛以前電影風格的產生也是因為環境的關係,他拍片都在晚上,因為晚上人少,不吵,好操作;而高達(Jean-Luc
Godard)的《斷了氣》(Breathless)裡的跳接(jump
cut),當初也是想把對白剪短,結果變成一種風格」。《呼吸》風格化的灰藍色調及跳接剪輯型式也是因為製作環境造就的一種典型。
何導演表示因為當時他們都是用過期底片拍,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暗房技術來處理;他們這次是使用跳漂白,感覺還蠻適合這個片子的步調,此外當時使用的零頭片其實都很短,所以無法拍太長的東西,變成有時候出來的鏡頭很短,很跳。此次的聲音處理出自國際知名的杜篤之之手,杜大師在聲音的製作上以反差性較大方式凸顯何導演想要的那種不安定的感覺。
誠如何導演所言:「拍片是跟著感覺走。」那個廣告風格強烈、如夢似幻的沙發場景並非精心設計而成,而是何導演出外勘景時在華中橋下發現的。當初看到沙發就在那裡,何導演覺得可以用在《呼吸》裡就把它放進來了。
但《呼吸》畢竟是比較屬於個人的影片,在面對商業要求時,是否能全然跟著感覺走呢?其實這個問題就回歸到“製作環境”了!像為發現科學頻道(Discovery
Channel)拍東西,或拍電視廣告時,那就是集體創作模式。發現科學頻道或廣告本身就有它的一種形式存在,就要跟著這個形式走。對何導演來說,這些創作模式都是一種對導演的訓練。
談到形式或風格的養成,很難不讓人好奇何導演平時喜歡看哪些類型或哪些導演拍的影片。何導表示,不一定只會看一些電影大師的藝術作品,也看好萊塢片。不過坦白說來,何導很欣賞香港導演杜琪峰和Peter
Jackson的作品!此外,伊朗導演阿巴斯作品的境界是何導認為自己無法達成的。
多元的電影圖像
一部15分鐘的《呼吸》,對不同地域的人來講,吸入相同的影音,卻呼出不同的情緒與想法。對何導演而言,這是有趣的,也是令他感到高興之處。因為他認為:影像創作由我來,把感覺留給觀眾吧!
對台灣的觀眾而言,看到《呼吸》的直覺反應就是SARS,而愛好自由的法國觀眾則對影片中戴口罩這件事感到恐懼不安。同樣地,其他的情結也因為不同的文化思維與意識形態,看出不同的觀點。如影片的開頭,我們聽到一個聲音叫道:「站住!戴上口罩…」緊接著出現警察追逐一光頭男子的景(一個犯人的象徵),歌詞裡也出現:「…我連呼吸都要小心」,如此的情節建構在何導演所創造出的虛擬世界,法國觀眾看到的是政治或制度的批判。這點何導演當初倒沒刻意安排,整體創作仍舊是“跟著感覺走”。
但創作的靈感並非是雜亂無序的,何導演當初拍這部片的時候曾告訴自己:拍出來的影片不要太像台灣片。何導演的理由是,台灣電影有一種特殊語言和調調,拍出來的東西很在地化,不管在取材上或風格上都是。這些東西不是不好,而是太多了!在《呼吸》裡,何導演企圖建構的是一個世界末日的基調,而這個世界不是指“台灣”,而是世界的某個地方,讓每個地方的人看了能對自身經驗有所聯想。如同亞洲觀眾看到的也許是SARS,但對現在的南亞人或歐洲人看到的也許是禽流感;對其他觀眾而言,也許是新一代的病毒入侵。為了讓《呼吸》更貼近觀眾,何導演要求攝影師使用特寫鏡頭,使觀眾感受到一絲絲窒息的美感,同時也讓觀者在鏡頭的凝望下,體驗別於台灣電影貫有的影像風格。
何導演對電影的執著與使命感並非建構於文化的傳遞或對國家民族的強烈情感。他表示目前為止在任何國家都沒有一種歸屬感,他都覺得自己在那裡都是個外國人,包括他出生的國家─馬來西亞。而目前在台灣拍電影,他希望拍攝的題材不要侷限於個人成長經驗題材,他想要拍的主題是有活力、更多元的。
|
| |